
| « | November 2025 | » | | 日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 | | | | | |
|
| 统计 |
blog名称:小雨
日志总数:262
评论数量:1273
留言数量:15
访问次数:4693066
建立时间:2005年1月8日 |
| 
|
W3CHINA Blog首页 管理页面 写新日志 退出
| 回复:洛丽塔 |
|
nrzj(游客)发表评论于2007/2/26 15:51:04 |
重读《洛丽塔》随感(代 译 序)廖世奇
第一次读《洛丽塔》差不多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当初的心态恐怕和不少今日的读者相去不远,只为听说这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名著,而且被禁过,从一本写得极其粗放的美国文学史上看来的故事梗概读着也确感新奇,于是就“大胆地拿来”英文版本,记得读时相当吃力,层出不穷的生词、僻词还在其次,最要命的是情节的展开慢得出奇,但同时似乎也使我确信了此书的不凡!现在看来,《洛丽塔》果然影响了世界文坛,而且似乎影响越来越大,难怪英国某家图书杂志把它列入二战以来影响世界的一百部书之中。 纳博科夫当时虽说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与卡夫卡、乔伊斯齐名,但让人总觉得有点儿隔膜,好像还不如成就在他之下的库特·冯尼格、约瑟夫·海勒来得亲切。意识流、荒诞、黑色幽默一类的流行标签似乎在此都不适用,就连被用得大而不当的“现代派”一词恐怕也很难派上用场。或许并非纯粹出于偶然,我们认识纳博科夫并不是因为他自视为传世之作的《洛丽塔》,而是更具“荒诞”意味、因而更容易被归类的《普宁》。《洛丽塔》的中文本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出版的,中译本俗丽的包装全然没有那种经典式的清高姿态,却露骨地透着讨好、挑逗的商业炒作的味道。《洛丽塔》被装扮成一部“非道德”的、严肃的艺术经典,其中的虚实读者自然心知肚明。不过,真有耐心读上几页的读者想必很快就会开始猜疑,《洛丽塔》竟是这样的“非道德”,这样严肃的吗? 纳博科夫在一九五四年春天将《洛丽塔》完稿后,自知一个中年男人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畸恋故事在当时的文化氛围里一定会招致非议,所以,在朋友的劝告下,连真名都没敢署。但后来又怕一旦被发现,更会授人以柄,才鼓起勇气改变初衷。书稿先后遭到四位美国书商的拒绝,纳博科夫便只好到欧洲去试运气。第二年,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了《洛丽塔》。这家出版社曾因出版塞缪尔·贝克特、让·热奈等争议作家的作品而在知识界享有一定的声望。但纳博科夫并不知道这家出版社当时还出版一套有绿面包封的色情小说丛书,而他心爱的《洛丽塔》正是以同样的包封,分上下两卷出版的。究竟有多少购书者因此而被误导,我们不得而知,但大多数人的失望是不难想见的。《洛丽塔》无声无息地与《罗宾逊的性生活》《直到她叫春》之类的色情读物作了差不多六个月的伴,多亏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慧眼识才,将它封为一九五五年最佳小说之一,这才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格林的褒扬立刻招来了反对者愤怒的抗议,而格林也毫不客气地还以颜色。这场争执很快引起了美国文学界的注意,海外版的《洛丽塔》随之开始在圈内流传。一九五七年夏,《铁锚评论》(Anchor Review)以一百多页的篇幅刊登了《洛丽塔》的节录和纳博科夫撰写的后记《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书》。一九五八年,美国的普特南出版社终于出版了《洛丽塔》的美国版。虽然《洛丽塔》在美国没有惹上官司,但招来了更激烈的抗议和谴责。以前只能算是小有名气的纳博科夫顿时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洛丽塔》也一路蹿升至《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第一位。争议的焦点自然是有关艺术的社会责任问题,但纳博科夫独特的叙事风格同样令批评家们感到不适。《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称:“《洛丽塔》无疑已经是图书世界的一桩新闻。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坏消息。……”这种评价或许纳博科夫并不放在心上,但令他颇感气馁的是自己的不少好友也有类似的看法,包括判断力不可不谓敏锐、而且向来推崇纳博科夫才华的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和著名小说家玛丽·麦卡锡。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都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表面的淫辞淫意,从而忽视了小说的艺术价值的缘故,但这种解释就好像魔术师用一个魔术来解释另一个魔术一样于事无补。 纳博科夫曾抱怨说他的批评者被故事本身的色情意味误导了,这恐怕只说对了一小半。尽管许多人的阅读动机可能确实出于要看一看《洛丽塔》到底有多“不道德”,但稍有耐心的读者不出几页,便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受了商业炒作的蒙骗。但话又说回来,小说故事本身总应该说是“不道德”的,而这其实也恰恰是《洛丽塔》曾一度遭禁的原因。问题在于,《洛丽塔》的“不道德”并非一般读者习惯上期待的那一种。道学上或许会觉得它低级下流,令人作呕,但猎奇者恐怕不会这么想。所谓“不道德”的艺术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而性、色情则是其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主题。《洛丽塔》虽说不乏性的描写,可似乎总带有一股子令人气馁的“性冷淡”。它既没有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的那种细腻撩人的感官快感,也没有乔伊斯《尤利西斯》里的那种满不在乎的猥亵。或许人们已习惯将《尤利西斯》中的色情段落看作是艺术无拘无束的纯粹性的证明,但纳博科夫坚决认为那是他极为推崇的现代大师的最大败笔。在《洛丽塔》的《引子》里,纳博科夫特意说明亨伯特的独白出奇的干净,绝无一般色情小说使用的下流的陈词滥调。他对色情本身不感兴趣,对以色情来证明艺术的自由似乎也并不关心,因为后者对他来说早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色情”不一定就是“不道德”,“不道德”也不一定就是“色情”。以为彼此相当,因而大呼上当的读者恐怕只能怪罪自己。但这还不是《洛丽塔》争议的关键,最令人难解的是,纳博科夫对道德问题本身也显得兴趣缺乏。纳博科夫当然明白亨伯特狂恋洛丽塔会触动社会的道德神经,但他始终不想追究亨伯特暧昧行为的社会内涵和道德后果,这又使他区别于《安娜·卡列尼娜》的托尔斯泰和《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纳博科夫既没有挑战社会道德规范的雄心大志,也没有普渡欲海众生的情怀,没有批判和嘲讽,也没有感伤和警喻。他讨厌任何有关他的小说是不是道德的提问。在《洛丽塔》的世界里,艺术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是在道德之外的。在这一点上,纳博科夫似乎还不如他笔下疯疯癫癫的亨伯特有道德感。亨伯特即使是在全神贯注地捕捉最销魂夺魄的欲望细节时,也不时扯进令他倍感煎熬的道德困惑。纳博科夫对此如何解释呢?很简单,亨伯特是亨伯特,纳博科夫是纳博科夫。他说:“深感亨伯特同洛丽塔的关系不道德的不是我,而是亨伯特自己。他关心这一点,而我不。”纳博科夫的意见当然不是说亨伯特同洛丽塔的关系是道德的,而是说这个问题与他的小说艺术毫不相干。不是对立,而是无关。 但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无关”。既然纳博科夫明明知道故事本身在道德上的挑衅性,明明知道让一个性变态者喋喋不休地追述自己欲望历程的所有细枝末节只会更深地刺激读者的道德神经,为什么又要求读者绝对不要追问任何道德问题呢?这种艺术姿态高得岂不有点儿蛮不讲理?其实,在纳博科夫看来,这正是对读者最好的调侃。他决心要在最容易引起追问的地方使道德变成一个最易见然而又最问不出名堂的问题。我们在此不妨拿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与《洛丽塔》作一简短的比较。《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可夫为了钱谋杀了一个当铺女主人(不幸还意外地杀死了她的妹妹),但他激动地说服自己绝不是一个普通的谋财杀人犯,竭力寻找种种形而上(尼采式的超人哲学)和形而下(使自己姐姐免受为钱嫁人的耻辱)的理由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然而,无论他的声音听上去多么动人和雄辩,却始终受到不同声音的挑战。我们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拉斯柯尔尼可夫的道德观,都无可避免地成为这个对话的一部分。就叙述结构而言,读者可能的道德追问可以说已预先成为《罪与罚》的对话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对话最终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它保证参与对话的声音都是认真和有意义的。相比之下,亨伯特比拉斯柯尔尼可夫“安分”多了。他从不挑剔道德约束的当与不当,从不为自己的行为寻找辩解的理由。对他来说,自己行为的不道德根本就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再去纠缠行为的道德含义实在是多此一举。我们可以厌恶他,却无法同他对话。亨伯特的世界始终是一个独白的世界,没有激情的辩论,只有无聊得令人绝望的口角。他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单调反复、琐碎芜杂的主观图景,推动情节发展的行为过程仅仅是这个图景的虚化的轮廓。他只求我们有全世界的耐心来聆听他被欲望烧灼的伤心史,包括一切飘忽不定、支离破碎的情感细节。纳博科夫知道读者不会轻易放弃固有的道德诉求,因而在叙事中预先把这种诉求变得如此绝对,如此不可怀疑,以至于在亨伯特自甘堕落的阴暗角落里不可能成为一个可供讨论的问题,而只能被当作一个纯粹是没有任何叙事意义的既成事实。纳博科夫在《引子》中说亨伯特的忏悔独白有着宝贵的病理学和伦理学价值,但似乎没有比这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了。事实上,我们要是真的去寻求这种价的话,就永远会被摒斥在《洛丽塔》的世界之外。顺便说一句,纳博科夫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向来没有什么敬意,认为《罪与罚》及陀氏的绝大部分作品算不上“真正”的文学。 作为作家,纳博科夫对道德的问题如此地不屑,对所谓“真实性”的问题也没有太多耐心。他曾把创作比喻为编造“狼来了”的谎言,常规意义上的“真实性”简直就像最后吃了说谎的小孩的大灰狼一样让他讨厌。《洛丽塔》其实在“真实性”的问题上是纳博科夫多产的创作中十分独特的一部小说,其描写给人的印象最接近经典现实主义的那种“逼真感”。但这种令人信服的“逼真感”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必不可少的背景,纳博科夫依然是一个醉心于操纵幻觉的魔术师。他说一切所谓的“真实”或“现实”不过是面具而已,并建议把这个词永远放在引号里。事实上,拷问《洛丽塔》叙事的“真实性”就如同拷问它的道德感一样令人气馁。除了简短的《引子》外,《洛丽塔》通篇都是亨伯特滔滔不绝的第一人称独白。但第一人称叙述常常就像无法佐证的一面之辞,并非绝对的可靠。读者一方面没有理由完全信任“我”的诚实,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更为可靠的客观依据。拉斯柯尔尼可夫狂躁的心理现实无论多么主观,都摆脱不了《罪与罚》第一人称的客观语境。相比之下,亨伯特活得轻松多了。尽管他在道德的审判庭上显得唯唯诺诺,毫无拉斯柯尔尼可夫式的倔强和勇气,却也演出了一场似是而非、狡黠得可疑的滑稽戏。比方说,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他那些看似负疚的忏悔到底有几分真诚,他是认真的还只是说给有崇高道德感的读者听的,或只是在对常规的忏悔文体进行模仿。纳博科夫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向来表示不屑,但他偏让亨伯特一脸真诚地追述自己恋童癖的根源、变态行为的动机以及被压抑的童年性经验等,仿佛我们读者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弗洛伊德信徒。纳博科夫不仅想让我们看看亨伯特的滑稽,似乎也想看看我们读者的滑稽。在他眼里,企图通过解读性象征对亨伯特做联想法治疗的读者可能比只想把亨伯特打入地狱的道学家更加可笑。纳博科夫刻意营造的这种似是而非的含混性令很多志在挖掘意义的阐释家感到无所适从。一位论者自觉找到了被这种含混性掩埋了的真义,称《洛丽塔》是“衰老的欧洲诱奸年少的美国”的象征,但另一位论者却在同样的地方有了别的发现:《洛丽塔》是“年少的美国诱奸衰老的欧洲”的寓言。纳博科夫劝读者不要在他的作品里寻找象征或寓言,滑稽模仿带来的含混性并不掩盖什么,它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精神,是通向纳博科夫所谓的“严肃情感的最高境界”的跳板。至于如何完成这一跳跃,则是对我们读者的又一个挑战。 纳博科夫对文学艺术有着简单而又苛刻的标准。他在《洛丽塔》的后记中这样说过:“对我来说,虚构作品的存在理由仅仅是提供我直率地称之为审美狂乐的感觉,这是一种在某地、以某种方式同为艺术(好奇、温柔、仁慈、心醉神迷)主宰的生存状态相连的感觉。”他以为达到这种境界的作品实在不多,其余一切都是垃圾,包括《堂吉诃德》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几乎所有作品。至于《洛丽塔》能否提供他所说的“审美狂乐”,只能端视每位读者的阅读体验了。
一九九七年六月于纽约
|
个人主页 | 引用回复 | 主人回复 | 返回 | 编辑 | 删除 |
» 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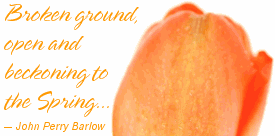

 [乐瑟温柔]洛丽塔
[乐瑟温柔]洛丽塔